两个月前,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作为建国后北京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性赛事,奥运会给这座本已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带来的交通压力不难想象。顺利通过考验的奥运交通到底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两个月前,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作为建国后北京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性赛事,奥运会给这座本已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带来的交通压力不难想象。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交通高层论坛上,奥运会期间直接参与交通规划和管理的各方专家,以“奥运交通的启示与奥运后交通”为主题,对奥运交通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到国外访问,对于奥运会期间的交通,国外的交通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全可靠,运力充足,优质服务。
“我感觉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确切的,而且国内外普遍对奥运交通的评价都比较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施仲衡说。
谈及此次奥运交通的成功经验,两院院士、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表示,奥运交通经验中突出的一点是,此次采取的很多措施和工程管理办法都不是只图一时之需。“我们不但解决了奥运会期间的交通问题,还可以解决今后若干年的问题。我们在奥运期间的交通规划和交通建设上,没有多花一分冤枉钱。”。
对此,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交通委原主任赵文芝说,北京市为服务奥运所购置的1000辆环保型公交车,现在还跑在大街小巷。奥运期间,北京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被提升到了200公里,还实现了道路系统的快速路网、主干路网、高速路网以及支路网全面大提升,这些成果在奥运会后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无一闲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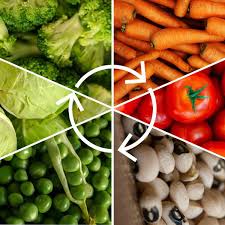
“北京市这几年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投入非常大,交通能力改善也非常大,但是这些改善实际上都是以城市的长远发展为目标的,极少专门为奥运会而做,这一点非常重要。”北京交通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郭继孚说,在整个筹办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工作的的核心任务是要满足城市长远的发展,而对于奥运会期间的特殊交通则主要采取制度化的管理。
“我觉得这次奥运会在交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非常宝贵,它对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大城市都有重要意义。”周干峙说。
一项数据表明,在奥运会期间,北京市居民的公交出行比例达到了45%,而在奥运会之前,这个比例为34.5%。公交出行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小汽车的出行比例则相应大幅度削减。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出公共交通在奥运的交通保障和城市运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交通保障,当时规划的开闭幕式的疏散时间才由90分钟缩短到开幕式75分钟、闭幕式70分钟,开幕式疏散的交通保障的成功,也使我们对整个奥运会交通树立了一些信心。”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说。
对此,赵文芝也认为,北京市政府决定奥运会期间以公共交通为主体,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次交通面临着机动车拥堵和环境的双重压力,最后市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赵文芝说,单双号限行保证了道路的畅通,但也给公共交通增加了沉重负担。
奥运会结束后,网上曾有一项关于“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你更喜欢哪种交通工具?”的调查。在这项调查中,有76.27%的网民选择了公共交通,其中66.1%的人选择了乘坐地铁。这些数据在说明公共交通为奥运会提供了强大支持的同时,也体现了公共交通的任务之繁重。
据悉,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在奥运会期间,北京市采取了缩短地铁发车间隔的措施。赵文芝介绍说,从一开始的5分钟一趟车,到之后的3分半钟一趟,最后一直到2分钟一趟,由此提高了将近70%的运力。
“作为一个城市,机动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机动化并不就意味着开小汽车,而更多应该采用节约化的公共交通运输方式。”刘小明说。
尽管如此,赵文芝表示,在奥运会之后,公共交通使用的强度仍需要进一步增强。当前北京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大概在36.8%,按这个比例,北京人均一天出行用公交的量是0.92次,这与东京、香港、伦敦等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公共交通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以地铁为例,目前北京市的地铁线网的密度依然不能够满足现有客流的需要,尤其是市中心客流需求。施仲衡介绍说,今年北京市二环以内的线,而巴黎市中心区线,纽约和伦敦的市中心线。“目前地铁线网的密度不高,直接导致了客流的大量集中,行车拥挤便成了必然现象。如何增加地铁的线网密度、提升地铁的营运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施仲衡说。
对于目前依然存在的交通拥堵问题,与会专家认为,交通拥堵是城市现代化、机动化过程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阶段,国际大城市在经济腾飞的阶段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也依然面临着这个问题。而一些奥运申办城市,如东京,在申奥成功以后和奥运会举办之前,也同样经历了交通大拥堵的阶段。这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北京目前的机动化发展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城市当年的发展速度,这就意味着几年时间内,北京就要面临发达国家城市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交通矛盾。
而对于奥运会期间为了防止交通拥堵而采取的管制措施,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王笑京表示,那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并不能持久。
“曾有专家提出,奥运会期间的交通是一个正常形式的交通,奥运会以前和以后的交通是非正常的,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奥运期间的交通并不是一个正常交通,而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王笑京说。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伦敦也面临着市中心车辆拥堵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03年3月开始,伦敦市政府开始实施拥堵收费。当年观测的结果显示,收费区域内的交通延误率下降了30%,进入收费区域的交通流量减少18%,居民乘坐公共交通的比例上升,这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到2007年,伦敦市区的运行时间和延误时间又恢复到征收拥堵收费之前的状态,而且还出了新的问题,即实施拥堵收费之后,征收费用的80%并没有用在改善公共交通和城市道路建设上,而是用在了维护设备和支付人员工资上。
“伦敦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借鉴。”王笑京说,行政限行措施对北京而言,也未必是一个能够持久的好方法,我们还需要再想其他办法。
王笑京表示,不应再用行政手段和管制型的政府思路去进行交通管理,“当我们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时,不能牺牲某一个群体的利益以获取另一个利益。以发展公交为例,大家是否坐公交应该是一种选择性的问题,而不是管制性地强制市民去坐”。政府在进行管理时应该在利用经济杠杆的同时,加强政府的服务和引导。“在这方面,你不能限制需求、不能限制发展,只应该给人多一种选择。”。